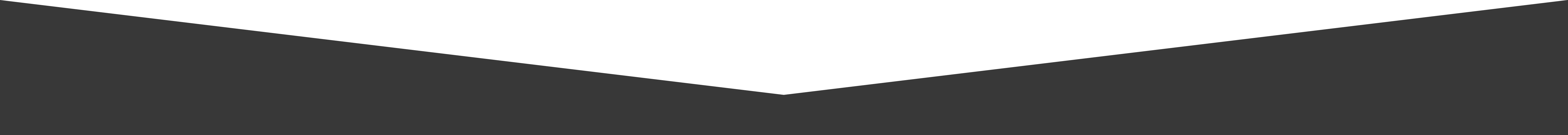定位點
樹豆湯裡的史前微光
更新:2025-05-19
人氣 515

阿改玩生活負責人/ Apyang Imiq程廷
「小黑人」的太魯閣語叫做msungut,字根來自sungut—「樹豆」,部落裡常見的農作物, 烹煮方法是將樹豆跟山肉或排骨一同熬,再加一些payi 1們種植的大白菜、高麗菜、紅白蘿蔔,或是隨處採集的龍葵、過貓、昭和草等。三石灶上,材火悶燒「部落總匯湯」,嘗起來味道豐富口感多元。樹豆調和山肉及排骨的肉腥味,蛋白質加上蔬菜纖維,提供滿滿的生活營養元素,每到春天採收期,喝上一碗樹豆湯就是當季的味覺記憶。
等等,小黑人叫做msungut。字首Ms加上樹豆Sungut,尺寸「像」…「樹豆」般這樣小,或是傳說神話中,老是躲藏在樹枝及果實之間的神祕生物,可愛又迷人的反派角色。湯匙裡的佳餚疊加傳說,有沒有吞嚥一鍋滿滿小黑人頭顱的感受。
如果有,那就是我們這幾年來,不斷投入Takaday史前遺址推廣及文化轉譯的核心初衷,同時也是我們的實踐熱忱及工作樂趣了。
2017年,我們社區發展協會承接花蓮縣文化局遺址文物展覽的計畫,自此多年走來,不斷地接觸Takaday,對史前文化產生難以描述及釐清的糾結情懷。同時擔任協會幹部、部落族人,或現在以青創公司負責人等多元角色,坦露直言,我常陷落於各式複雜人際關係,迷惘於族人文化、遺址保存發展,學術研究視角等各個切面之中。
但也許正因為如此,私心期盼支亞干,或是更多原住民部落/社群,嘗試長出更屬於地方,著力於各方權益關係群體,找出某種攪揉且開放,混雜又超然,既差異又普同,觀看或處置史前遺址的態度及方式。
支亞干遺址位於部落西南側,一片傾斜的緩坡台地上,族人稱為Takaday,這裡同時也是百年前遷徙至支亞干的眾多家族中,來自Tpdu-山棕茂密之地(如今太魯閣國家公園稱為天祥)的家族。Tpdu家族在Takaday上堆疊石牆,並搭築家屋、工寮及從事農耕或狩獵行為,傾斜山坡地整建為一處處優美梯田,是族人生活的重要據點。
耆老口述中,從前種植小米、玉米、紅藜、地瓜、芋頭等民族作物,戰後部落納入市場經濟,民族作物轉為部分自食,更多的人轉而投入種植硬質玉米、花生、油桐等經濟作物,並由農會或一般的平地盤商收購。60至70年代,隨著都市化發展,大量人口移往都市,Takaday出現許多造林補助用地,一棵棵列植整齊的樹於農地站立,更多的土地則在缺乏勞動力的狀況下變成荒地。
2002年臺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,再次重擊部落農產業,農會及盤商不再收購雜糧作物,高大玉米葉隨風飄逸的景致不再,山區缺乏平地完善的灌溉系統及機械化成本過高等條件,Takaday漸漸成為「只有老人會去工作的地方」。就此,部落自身山地平地化現象篤定,山上對眾多年輕人來說,是既陌生又熟悉的地景存在。
逐漸年邁的山上耕種人就此放棄了嗎?那些手掌因長年勞動長出深厚皮繭的payi及baki 2們,很快地迎接Takady的新風貌。
隨著花蓮觀光業興起,許多餐廳或熱炒店販售炒山蘇,成為遊客們必定品嘗的特色料理。近山多雨又潮濕的支亞干,自此興起山蘇的種植。從前造林的大樹底下,叢聚株株爬上大樹或驚險懸崖,從高處到低處,採集而來的山蘇。
在考古學家進入之前,Takaday早已發展百年以上的地方文化,甚至極有可能連結千年的史前史。
農人們頻繁撿拾到的玉器陶器,他們主張是小黑人使用的器具?或是族人主張Takaday特殊的地形是巨人踩過的腳印,在史前文化或考古研究中存在意義嗎?
若展開臺灣原住民族對小黑人及巨人的傳說,或是台東小馬遺址發現的「矮黑人」頭骨?我們真能十足把握地說沒有意義嗎?或者,讓我們嘗試釐清,前述百年的遷徙歷史,近代生活及農業型態的轉變,對同是史前遺址所在地的Takaday,地表上下累積的豐厚物質文化,是否毫無意義?
答案恐怕是否定的。
後過程主義考古學,認為物質文化並非僅是人類活動的「背景」,應視為與人類具有互動關係的「主體」(agency)。「物」本身不僅被動地反映人類行為,也主動參與到人類的社會與文化生活中。族人如何透過神話、傳說、以及當代經驗,主動地賦予遺址新的文化意涵,建立與遺址之間的互動關係,而非僅僅從客觀的歷史數據去詮釋遺址,是我認為臺灣原住民考古可發展的一種途徑。
下次,品嘗樹豆湯前,讓我們一起想想湯碗裡的史前微光。
「小黑人」的太魯閣語叫做msungut,字根來自sungut—「樹豆」,部落裡常見的農作物, 烹煮方法是將樹豆跟山肉或排骨一同熬,再加一些payi 1們種植的大白菜、高麗菜、紅白蘿蔔,或是隨處採集的龍葵、過貓、昭和草等。三石灶上,材火悶燒「部落總匯湯」,嘗起來味道豐富口感多元。樹豆調和山肉及排骨的肉腥味,蛋白質加上蔬菜纖維,提供滿滿的生活營養元素,每到春天採收期,喝上一碗樹豆湯就是當季的味覺記憶。
等等,小黑人叫做msungut。字首Ms加上樹豆Sungut,尺寸「像」…「樹豆」般這樣小,或是傳說神話中,老是躲藏在樹枝及果實之間的神祕生物,可愛又迷人的反派角色。湯匙裡的佳餚疊加傳說,有沒有吞嚥一鍋滿滿小黑人頭顱的感受。
如果有,那就是我們這幾年來,不斷投入Takaday史前遺址推廣及文化轉譯的核心初衷,同時也是我們的實踐熱忱及工作樂趣了。
2017年,我們社區發展協會承接花蓮縣文化局遺址文物展覽的計畫,自此多年走來,不斷地接觸Takaday,對史前文化產生難以描述及釐清的糾結情懷。同時擔任協會幹部、部落族人,或現在以青創公司負責人等多元角色,坦露直言,我常陷落於各式複雜人際關係,迷惘於族人文化、遺址保存發展,學術研究視角等各個切面之中。
但也許正因為如此,私心期盼支亞干,或是更多原住民部落/社群,嘗試長出更屬於地方,著力於各方權益關係群體,找出某種攪揉且開放,混雜又超然,既差異又普同,觀看或處置史前遺址的態度及方式。
支亞干遺址位於部落西南側,一片傾斜的緩坡台地上,族人稱為Takaday,這裡同時也是百年前遷徙至支亞干的眾多家族中,來自Tpdu-山棕茂密之地(如今太魯閣國家公園稱為天祥)的家族。Tpdu家族在Takaday上堆疊石牆,並搭築家屋、工寮及從事農耕或狩獵行為,傾斜山坡地整建為一處處優美梯田,是族人生活的重要據點。
耆老口述中,從前種植小米、玉米、紅藜、地瓜、芋頭等民族作物,戰後部落納入市場經濟,民族作物轉為部分自食,更多的人轉而投入種植硬質玉米、花生、油桐等經濟作物,並由農會或一般的平地盤商收購。60至70年代,隨著都市化發展,大量人口移往都市,Takaday出現許多造林補助用地,一棵棵列植整齊的樹於農地站立,更多的土地則在缺乏勞動力的狀況下變成荒地。
2002年臺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,再次重擊部落農產業,農會及盤商不再收購雜糧作物,高大玉米葉隨風飄逸的景致不再,山區缺乏平地完善的灌溉系統及機械化成本過高等條件,Takaday漸漸成為「只有老人會去工作的地方」。就此,部落自身山地平地化現象篤定,山上對眾多年輕人來說,是既陌生又熟悉的地景存在。
逐漸年邁的山上耕種人就此放棄了嗎?那些手掌因長年勞動長出深厚皮繭的payi及baki 2們,很快地迎接Takady的新風貌。
隨著花蓮觀光業興起,許多餐廳或熱炒店販售炒山蘇,成為遊客們必定品嘗的特色料理。近山多雨又潮濕的支亞干,自此興起山蘇的種植。從前造林的大樹底下,叢聚株株爬上大樹或驚險懸崖,從高處到低處,採集而來的山蘇。
在考古學家進入之前,Takaday早已發展百年以上的地方文化,甚至極有可能連結千年的史前史。
農人們頻繁撿拾到的玉器陶器,他們主張是小黑人使用的器具?或是族人主張Takaday特殊的地形是巨人踩過的腳印,在史前文化或考古研究中存在意義嗎?
若展開臺灣原住民族對小黑人及巨人的傳說,或是台東小馬遺址發現的「矮黑人」頭骨?我們真能十足把握地說沒有意義嗎?或者,讓我們嘗試釐清,前述百年的遷徙歷史,近代生活及農業型態的轉變,對同是史前遺址所在地的Takaday,地表上下累積的豐厚物質文化,是否毫無意義?
答案恐怕是否定的。
後過程主義考古學,認為物質文化並非僅是人類活動的「背景」,應視為與人類具有互動關係的「主體」(agency)。「物」本身不僅被動地反映人類行為,也主動參與到人類的社會與文化生活中。族人如何透過神話、傳說、以及當代經驗,主動地賦予遺址新的文化意涵,建立與遺址之間的互動關係,而非僅僅從客觀的歷史數據去詮釋遺址,是我認為臺灣原住民考古可發展的一種途徑。
下次,品嘗樹豆湯前,讓我們一起想想湯碗裡的史前微光。
註1:Payi 太魯閣族語女性耆老。
註2:Baki 太魯閣語男性耆老。
相關照片